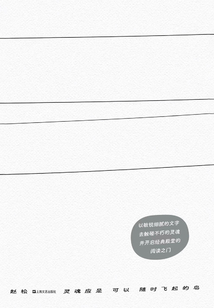
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
最新章节
书友吧第1章 戏剧是世界解体与重生的临界点
关于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
无论如何,瑞典文学院把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久负盛名却备受争议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是需要魄力的。自从1999年汉德克抨击北约大规模轰炸南联盟过程中伤害平民的残暴行径,就被西方主流舆论不时口诛笔伐。2006年,他又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秘密葬礼。结果2014年他荣获“国际易卜生奖”时,就被西方重要媒体和批评家斥为“史无前例的丑闻”、“等于把康德奖颁给戈培尔”。
向来特立独行的汉德克,面对世界的态度始终是:“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任何政治目的,质疑任何“政治正确”。他不能容忍文学上的保守和不思进取。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是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是为了破除任何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而存在的。
1966年4月,在德国著名文学团体“四七社”的美国年会上,24岁的汉德克尖锐地批评了德国当代文学墨守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两个月后,当《骂观众》在“法兰克福实验艺术节”上首演时,这部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事件、没有对白……从头到尾只有四个无名者在不停说话、冒犯观众并演示着对传统戏剧的彻底否定与颠覆的戏剧,使汉德克在争议声中开始备受瞩目。
在欧洲现代主义以来的先锋戏剧谱系里,汉德克颠覆传统的精神与在形式创新上的贡献,完全可以跟阿尔弗雷德·雅里、阿尔托、尤内斯库、贝克特等大师相提并论。就像柏林艺术节主席奥伯恩德曾说的那样,汉德克是少有的能将戏剧向前推进一步的剧作家。
从一开始,他的戏剧就直指“语言”本身。在其戏剧观里,“语言”是使一切存在生成与瓦解的根本要素。语言本身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使“人”成为语言激流里浮沉隐现的泡沫。而戏剧舞台,只能是呈现语言导致的人与世界的解体与重新生成的临界之点。
暧昧的“我”的无所不是与无所是
在文景版的《骂观众》里,收录了汉德克三个早期剧作:《自我控诉》《骂观众》和《卡斯帕》,以其关联性和演进性呈现了汉德克戏剧创作的脉络。
《自我控诉》篇幅短小,但作为先声,它已明确展现了汉德克的戏剧观和方法论。汉德克称之为“朗诵剧”。它没有角色,主要通过两个朗诵者的“声音相互配合……声音的大小变化鲜明,以制造听觉层次”,而舞台是空的,不使用幕布,演出结束时也不落幕。在这部剧作里,传统的戏剧因素荡然无存。它从一个人的诞生讲起的,然后讲“我”从小到大的变化——尤其是“我学会了词语”,“我变成了句子的对象”,“我学会了会干这干那”,“我生活在时间中”。随后,“我被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掌控了。我有个人的信息。我被变成了一个有档案可查的人。我有自己的灵魂。我被与生而来的罪孽玷污了。我有自己的比赛号码,我被列入了比赛者的名单里。我有病了,我被变成了病历中可查的人。我有自己的公司,我被商业登记在册了。我有自己的特征,我被固定在人物描述中了。”
所有的一切听起来都是既具体又抽象的。汉德克关注的是“人”的意识的变化。当读者觉得“我”已渐渐清晰时,却发现作者已通过“我”成年后的罪与罚、义务和责任的确立,引出了对所有“冒犯”行为的疑问,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表明态度”的方式,其中充满了犯规违禁、不合时宜,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另类言行,而更为重要的:
“我没有在意语言的规则。我违反了语言的规则。我说了没有思想的话。我盲目地赋予世界上的物体以种种性质。我盲目地把表示物体的词语赋予表示物体性质的词语。我盲目地用表达物体性质的词语观察了世界。我说物体是僵死的。我说形式多样是多姿多彩的……我说道德是虚伪的。我说界限是模糊的。我说竖直食指是道学的。我说怀疑是有创造性的。我说信任是盲目的……我说正直是知识分子式的。我说资本是腐败的。我说感觉是迟钝的。我说对世界的认识是扭曲的。我说意识形态是假的。我说世界观是模糊的……”
“我”是无所不是的。人有的问题“我”都有。“我”是善的也是恶的,有各种错误和不合时宜,既释放纵容了所有欲望,又承受了一切后果。“我”即是每个人。而这场“自我控诉”所针对的,正是所有人的“自我”,进而揭示“我”的无所是。最后,面对死亡阴影的临近,“我”的结论是:“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曾经不是应该是的那个我。我没有变成我应该成为的那个我。我没有保持应该保持的。”而比这个貌似虚无的结论更为重要且深刻的,则是结尾:“我来到剧院里。我听了这部剧。我朗诵了这部剧。我写了这部剧。”
让剧场解体的“骂观众”
在《骂观众》里,汉德克要做的是对传统剧院和观众的审判与解体。它是“说话剧”,没有人物,只有四个说话者。在汉德克提供的有17条要求的《演员守则》,关键词就是“仔细倾听”和“注意观察”,而内容则已暗含对观众的讥讽,尤其是最后两条:
“注意观察动物园里那些模仿人类的猴子与那些吐口水的美洲驼。注意观察那些懒汉与游手好闲者在街上走路和在考虑机上玩游戏时不同的神情。”
在开场前的那个说明里,汉德克在细致地描述了传统剧场里的一切现象之后,就先行把要骂的主要句子说出来了:“你们这些丑恶的嘴脸,你们这些小丑,你们这些傻呆呆的眼睛,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家伙,你们这些活宝,你们这些只知道张着嘴巴傻看的蠢货。”
全剧62段文字,除了前面几段是明确告知观众,这不是一场戏剧演出,不会有他们想要看到的情景,也不会满足他们观看的乐趣之外,一直到第47段,作者都在不遗余力地质疑并审判传统戏剧、剧院和观众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因为“在这里,戏剧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利用。可能性的范围并没有被充分测量。戏剧并没有被解放。戏剧被束缚了。”
这场戏的主角不是舞台上的说话者,而是下面的观众:“你们就是主题。你们是核心。你们和我们演对手戏。这一切针对的都是你们。你们是我们话语的靶子。你们充当的就是靶子。这是一个隐喻。你们是充当我们隐喻的靶子。你们充当隐喻。”
在整出戏里,无论怎么说如何骂,都是表象。最核心的其实是:“这出戏是一个引子。它不是另外某一部戏的引子,而是有关你们所作所为的引子,包括你们曾经做过的,现在正做的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你们是主题。这出戏就是关于主题的引子。”换句话说,这出戏的主体并不在舞台上,而是在观众那里——观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现场反应,都是这出戏的内容。在这里,与传统意义上的剧场、舞台概念一起被颠覆的,还有“观众”的概念——他们变成了被肆意挑衅嘲骂的戏剧主体。在世界戏剧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戏剧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骂观众》为很多年以后才开始在当代艺术里出现的将行为、表演和现场互动融为一体的艺术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卡斯帕的自我重生与解体
很多人认为《卡斯帕》的成就远高于《骂观众》,这是因为它在骨子里其实是相对传统的。尽管在形式上它更进一步延展了《自我控诉》和《骂观众》开拓的道路,但从对戏剧因素的内在运用来看,它又向“传统”做出了某种“靠近”。但这并不是妥协或退缩,而是汉德克要在颠覆传统的废墟上寻求创新的可能。
首先,这部戏是有“人物”的——卡斯帕·豪泽。其次,虽然作者开篇即声明:“剧本《卡斯帕》表现的不是卡斯帕·豪泽现在发生什么,或者过去发生什么,而是一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它要展示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说话而学会说话。”但是,卡斯帕显然是有过去的。从他那支离破碎的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过去的迹象和信息。他参加过战争,幸存的是其肉身,被毁的是其灵魂,是其自我意识和语言系统。就像一台系统崩溃的电脑,他需要重装系统及各种软件,要借助语言恢复自我的意识思维系统并实现重启,否则他就什么都不是。
一个不出场的旁白者试图通过语言帮助指导卡斯帕学习恢复语言能力。而卡斯帕最喜欢说的句子是:“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旁白者的指导是灌输式的、指令式的、诱导式的,也是道德说教式的,经常充满了清教主义的心灵鸡汤意味,喜欢强调秩序:“你是一个句子幸运的占有者,它将会为你使任何不可能的有序成为可能,使任何可能和真实的无序成为不可能:它将会为你驱走任何无序。”
然而,近乎悖论的是,似乎卡斯帕的语言系统崩溃得有多彻底,他这个人就有多固执:“人家教给他说话的本领,他想保留自己的句子。”这是因为在旁白者的教诲话语中,不仅包含着规训、告诫、心理分析及对秩序的反复强调,还包含着强烈的控制欲。很多时候,这位旁白者的话语听起来甚至有点像上帝。于是问题就来了,卡斯帕意识到自己被控制了。他出现了人格分裂——舞台上出现了多个卡斯帕,他们像一般戏剧人物那样表演着各种手势,讽刺地模仿着卡斯帕说话,制造各种能够干扰卡斯帕的噪音,迫使他用锉刀在麦克风上锉出对抗的噪音……最后,卡斯帕反复念叨着:“山羊和猴子”,而沉重的帷幕缓慢移动,直至撞倒了所有的卡斯帕。
一般来说,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山羊,则象征着创造力、活力、攻击性、性欲,甚至是撒旦的象征;而猴子,则象征着邪恶、贪婪和盲目崇拜,或是异端。当汉德克把这两个象征交由恢复语言能力的卡斯帕来反复念叨并作为全剧的结尾时,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他的意图里或许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语言的生成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象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象征,是人作为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的象征,但是,语言并不只是导致文明诞生、宗教与信仰的诞生,也会催生制造邪恶,也会制造战争灾难。
同样道理,要是以为恢复人的语言能力就意味着恢复人的理性存在,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在本质上就充满暧昧与不确定性的语言里,从来都是既有上帝又有魔鬼的。在汉德克的笔下,无论旁白者如何费尽心力,卡斯帕如何努力学习恢复,都无法摆脱那个作为人与世界解体和重新生成的临界点,甚至连这个点,最后也会失去。
2019年10月20日

